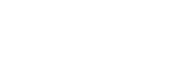清明忆先师
陈力
又是一年清明时,思念的闸门再次被拉开。我只能用苍白无力的文字,还原与先师们交往的点点滴滴。但这些文字终究是徒劳的——记忆里的温度、气息、声音,都像隔着毛玻璃看到的烛火,影影绰绰却触不可及。墨迹干涸时,所有鲜活的细节都会凝固成单薄的符号。但除了这样的书写,我又能如何阻止他们消失在时光的褶皱里呢?
点点滴滴忆霍老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006年,我有幸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更为幸运的是,在这所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学府里,遇到了一大批学识渊博、令人敬仰的大学者、好老师。霍松林老先生便是其中重要一位,尽管当时他年事已高,不再上台讲课,我也仅仅见过他两次,但我与老先生是“颇有缘分”的,他对我的影响从大学时代延续至今。
甫入大学,在开学典礼上,校领导对主席台上一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者介绍道:“这是我校文学院名誉院长、著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霍松林老先生!”当时已85岁高龄的霍老颤颤巍巍起身,微笑着向台下师生致意,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并见到老先生。
大学期间,一直未能再与霍老见面,但与他的缘分始终在加深。大一大二时,刘生良老师为我们讲授古代文学史,他是霍老的“嫡传弟子”,师从霍老攻读博士学位。他经常给我们讲到霍老精深的学术造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们钦佩不已。大三的时候,霍老的老乡、甘肃天水师范学院的霍志军老师在陕师大文学院读博,也兼职为我们讲授古代文学史,他当时在进行一些关于霍老治学方法与诗词创作的研究,我偶尔帮霍志军老师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他赠送了我一本《霍松林诗词集》。得到诗集后,我仔细研读、受益颇多,欣逢霍老又荣膺“中华诗词终生成就奖”,我“敝帚画西施”,写下了《高歌唐音,重铸诗魂——霍松林先生诗艺欣赏》,拙文最终在《陕西师大报》上发表。文章发表后有幸被霍老看到,他还打电话给校报编辑部的老师,询问我的有关情况。大四第一学期在西安市太乙路中学实习,指导老师是退休后又被中学返聘的张振宇老师。他一听说我是陕师大文学院的学生,马上就说道:“你们文学院的霍松林老先生很厉害!”又立马翻出教参中霍老撰写的《赏析》一文啧啧称赞。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大学毕业前夕,我还能有面对面接受霍老勉励的机会。2010年6月,骊歌声起时节。一天清早我还在睡梦中,辅导员杨国庆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立马赶到学校大门口,说要到老校区去拜访霍老,录制霍老寄语文学院毕业生的视频。我一跃而起,迅速穿衣洗漱,往学校门口飞奔。同行的还有我的同级同学王思齐、刘湘吉,学校宣传部的吴国彬老师,还有一个摄像老师。约莫半个小时,来到了霍老家中,会面地点放在了家中的书房兼客厅,他仔细询问了我和王思齐、刘湘吉的具体情况。当时,霍老已近90岁高龄,我们只说了一遍,他却清晰地记住了我们三人的姓名和即将就业、读研的有关情况,视频录制也是一遍就完成。至今我仍记得,他对我们说,不管继续读研还是工作,都要认识到学习是持续的过程,要养成终身学习、虚心求教的良好习惯;做人应坚持原则、勤勉上进,淡泊名利、堂堂正正;要将踏实工作、认真研究和用心做人统一起来,不让流年虚度,不失人生精彩。他还特意叮嘱即将在基层就业的我,万事开头难,要尽快适应工作环境,获取从业的资本与信心,与同事处理好关系。
拜访即将结束时,霍老欣然同来访的师生合影,还和我们三个毕业生分别合影,我当时就后悔因为赶时间,自己的穿着太随意。霍老还将自己的著作签名赠送,勉励我们努力上进。他给我们三个毕业生每人送了三本著作,边签名边说,自己手抖得厉害,握笔有些困难,每个学生只签名一本,让我们见谅。
我们即将走出他家大门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了我们,慢慢地把我们领进卧室,里面坐着一位显得病恹恹但面容慈祥的老奶奶。霍老在老奶奶的肩膀上拍了拍,像介绍“宝物”一样说道:“这是我的老伴,她叫胡主佑。”我们向老奶奶问好,老奶奶也微笑地回应了我们。
霍老寄语的视频在文学院毕业生答谢晚会上播出后,学生们深受感动。我将视频珍藏在了电脑里,霍老赠送的三本著作我也放在了书柜最显眼的位置,即使工作再忙再累,也时常看上一阵儿,感觉又获得了无穷的力量。
2017年2月1日,惊闻霍老驾鹤西去的噩耗,我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不禁潸然落泪。2021年,霍松林先生诞辰100周年。看着与老先生的合照,摩挲着老先生给我的签名,老先生爽朗的笑容、浑厚的声音仍经久浮现。写得再多,也深感自己的文字是孱弱无力的,最后且借用校友的文字表达大家共同的心声:“霍老是巨人、是根基、是灯塔、是灵魂,是我陕师大文学院学生挺直腰杆的底气,是低头自省的警醒,铭记先生‘扬葩振藻,绣虎雕龙’的期许!”
一面成永远
2024年10月24日,我翻看微信朋友圈时,突然被一位媒体老师发布的消息惊呆了:薛保勤兄长因病抢救无效,于2024年10月24日8点24分在西安辞世。心里咯噔一下的同时,瞬间泪蒙双眼。
最早知道薛保勤老师是在2009年。第二届中国诗歌节论坛活动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当时我正在学校就读,作为诗歌发烧友有幸参加活动。在随会配发的诗歌杂志上,我第一次拜读了薛老师的诗歌作品,一下子被深深吸引。2011年秋天逛世园会的时候,尽管不巧遇上了大雨,但广播里传来荡气回肠的世园会主题曲《送你一个长安》却让人为之一振。“送你一个长安,蓝田先祖,半坡炊烟,骊山烽火,天高云淡,沿一路厚重走向久远。送你一个长安,恢恢兵马,啸啸长鞭,秦扫六合,汉度关山,剪一叶风云将曾经还原……”不禁感叹道:怎样的胸襟和境界,才有这般摄人心魄的手笔!也只有薛老师,或者说是薛老师这一类人,才有如此的手笔!
之后一直拜读薛老师的文章,购买过他的著作,陕师大出版社也赠送给我一些薛老师的书籍。对薛老师的敬仰,在意的并不是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这些头衔,而是始终把他看成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作家、诗人、词作家。
一直未敢奢望有和薛老师碰面的机会。2023年11月3日中午,意想不到的惊喜突然而至,电话得知薛老师马上要到老县镇采风的消息。立即乘车到老县,在龙泉山庄等了不一会儿就见到了薛老师,和猜想中的一脸严肃不同,他清癯的脸庞上有着满满的和蔼温善。
交流了一会儿后,我从包里取出一本《风从千年来》请薛老师签名。不料因为看了很多遍,扉页连接处开了胶,薛老师用手细心整理了一下,之后在扉页写下:“陈力小友存正:心中有缘,就有春天;心中有禅,就有恬淡。薛保勤,2023.11.3”。
两天的见面交流中,基本上都与创作有关。交流的时候,薛老师的爱人姚慧琴老师在旁边静静听着,很少说话和插话。
“心随天地走,意被牛羊牵,大漠的孤烟,拥抱落日圆,在天的尽头,与月亮聊天……”在此之前就听过的唯美动听的《敕勒歌》,竟不知是薛老师根据南北朝民歌重新填词的。我说,好多地方用了,竟然连个名字都不给署,把老师的功劳给埋没了。薛老师只是淡淡一笑说,没啥没啥,有人喜欢就行,就当为大家增加“一乐”吧。
当时我写了一首诗歌,自己还觉得比较满意,请人配音朗诵还制作成视频。薛老师听完后进行了鼓励,之后耐心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提高之类的,只可惜事情一直都多,加上自己水平有限,诗歌至今还是原封不动放在那里,辜负了薛老师的一片热心。
知道我在从事新闻写作后,他细细传授给我一些新闻写作的方法与技巧。见面的第二天,我邀请薛老师前往大贵镇采摘皱皮柑,他欣然答应前往。在后湾村的垭坪,黄澄澄的果子挂满了枝头,像一个个精灵在枝头跃动。薛老师心情很放松,开开心心摘下一个柑子,剥开吃了一瓣,笑盈盈地说:“还好,不是太酸!”返回下山的过程中,薛老师感慨沿途的徽派民居盖得好、真漂亮。在黄洋河畔的小广场,我邀请薛老师和他爱人进行了合影留念。
11月5日上午,薛老师离开老县返回西安时,我因有急事未能到场送行,只能通过微信草草告别。“听陕师大宣传部的老师说您有一个别号——薛大帅呢。”“没有没有,他们说着玩的。”“薛老师,路上慢点,欢迎以后常来!”“谢谢陈力的热忱与周到,喜欢浓浓的书卷气。”
薛老师返回西安后不久,给我邮寄了《薛保勤词作词:问天》《送你一个长安》两本作品,都细细留了言、签了名。
有人评价薛老师,“他把诗当作歌来写,把歌用诗来展现。”知道《敕勒歌》的词是他的手笔后,我愈加喜欢,一天要听很多遍,五音不全的我还学着唱。微信聊天我说给他后,他发给我不同的演唱版本,有十几种之多。让我受宠若惊的是,有一天他说自己准备出一本书(后来才知道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的《岁月八记》),写了两个不同风格的后记,问我喜欢哪一个,让我进行评价。2024年央视春晚由薛老师作词的《花脸》走火后,他饶有兴致地给我讲述了和春晚合作的经过。有人这样的评价颇为精当和形象:这首《花脸》带着黄土地秦腔的嘶吼声,走遍全球,折服华人、征服老外,在世界各地的角落里炸裂地叫响。
见面的时间只有两天,多为微信交流,情谊却是弥足珍贵的。2023年底到西安出差,本想见薛老师一面的,结果不巧他到外地出差。今年4月中旬,本想请薛老师再次来平利采风,并想请他为平利县写一首歌词的,结果他因为还很忙,回复道:谢谢,择机!6月份的时候,全省“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在安康举办,提前得知薛老师要参加活动,心里不禁一阵惊喜,结果他没能参加,心里因未能再次见面失落了很久。
和薛老师的初见,却是最后一面;一别,竟然成为永别。生命无常,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情是十分沉痛和煎熬的。长者风范,先师之恩,岂敢忘?岂能忘!
忆红柯老师
2018年2月24日,原本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但突然惊闻红柯老师病逝。他岁数并不大,以前讲课他说过自己喜欢慢跑和冷水浴,身体应该不错,是不是误传消息?除了不相信,还是不相信。但接下来铺天盖地的消息,不得不让人接受这一令人心痛泪下的现实,白天不安,深夜无眠。
2006年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听闻红柯老师的大名,《西去的骑手》《金色的阿尔泰》《跃马天山》《黄金草原》《太阳发芽》《咳嗽的石头》《手指间的大河》,连作品名都散逸着浓浓的诗意。见面认识他,是2008年到了长安校区,旁听他讲授的选修课《文学与人生》,我还是课堂的“编外学生”。尽管是大课,但他的课太难抢到手了,只好偷偷旁听。仰慕已久,终见真人,难抑激动,第一堂课后我就问他要签名,他问了我的名字,思忖了一会儿,然后提笔写下“大美无言——与陈力同学共勉”。“大美无言”,简单四字,无限关切勉励之情尽含其中。
张宗涛老师在文中写到,总觉着红柯是一瓶度数很高的烧酒,平时装在瓶子里,冷冰冰地凛冽着,要不贴标签,看不出有多么珍罕,但他其实是一瓶能让人热血沸腾的烈酒,盖子一开,就已经酒香四溢。我觉得这种描述太贴切了。初见老师,普通的长相,普通的穿着,并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一开口讲课马上就不一样了,稀疏卷曲的头发下,满脑的智慧和才思喷涌而出,绘声绘色,语速极快。即使偶有停顿,也是满脸思虑。他是十分热心肠的,急不可待地将自己的沉思告诉给学生们,抚慰他们的浮躁,缓释他们的焦虑,卸下他们的迷惘。他是十分谦和的,结合自己的作品讲创作时,除了讲创作过程外,就讲不足和遗憾。如同大厨讲做菜,只讲怎么备料、怎么烹制,还可以怎么提高,从来不讲自己做的菜好看好吃。
通过听课和课外阅读,对红柯老师的创作有了更多的认知。红柯老师说,他不相信天时地利人和,杰作都是人生最悲惨最黑暗的时候写出来的,都是带血带泪的,都是百强相遇勇者胜。必须保持元气,绝不分散精气。切·格瓦拉说过,“我走上了一条比记忆还要长的路。陪伴我的,是朝圣者般的孤独。”红柯老师就是文学的朝圣者,把生命之光聚在一处,一生只干一件事,一生只做文学的歌者舞者。
在我的老家,勤劳的老农不管严冬,还是酷夏,清晨起床就扛着锄头下地,挖地时从不抬头,从一头挖到另一头,从一块到另一块,速度和深度年轻小伙看了都咋舌。红柯老师在文字的密林里,深挖地、细耕作,一锄头接一锄头,一季接一季。
12个长篇、35个中篇、100多个短篇,300多篇散文,总计800余万字。别说创作800余万字,在阅读快餐化、碎片化、娱乐化的今天,能潜心阅读800余万字的又有几人?学者、评论家但汉松说:“真正的阅读需要亲自把文字当药煎服,使其进入体内,和身心、血液、神经中枢发生奇妙反应,没有人能替你进行新陈代谢。”阅读如此,创作何尝不是?坚持手写,远离手机,极少应酬,红柯老师始终和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哲人的思考,一直苦苦追寻远方的梦想与诗意,提升生命的韧度和质感。他的生命成为巨大的熔炉,世间万物、人间温情在他体内集聚、发酵、翻煮,淬炼成文字里的人性、诗性和神性。
书道唯寂寞,创作是艰辛的,作品是带汗带泪带血的。如同父母抚育小孩,孩子白天扭来扭去,时间长了,带着胳膊生疼,晚上吵闹不停,被搅得心神不宁,但一直会保持着耐心。因为有无尽的爱,因为有无尽的情。红柯老师之于创作,就像父母之于孩子,是永远不会惜力的,这种爱,是无止境的,是无原则的。
如果问红柯老师心里装的除了文学,还有什么?我想那就是学生。不管他有多忙,上课之前他总是把参考资料和参考书目细细整理并打印好发给学生。我当时写诗的兴致正浓,将自己的习作整理打印了60多页,一次上课的时候拿着请他指导。他是那么忙,我料想他翻几页,总得给我说两句、写两句,就算很不错了。不想刚过了一星期,他把打印件还给我,并鼓励我坚持下去。我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每页都有红笔批改。指出存在问题,提出修改意见,提供参考书目。哪怕有一句诗是他认为还好的,都进行了鼓励。我心里激动之外,还觉得十分愧疚:为了我这些可以说是算不上诗的句子,花了他不少精力,耽误他不少时间。可惜毕业之后,工作忙碌,事情繁杂,一首诗歌都没写了,真是愧对他的殷殷期许了。
上了一学期的课,只记得一次红柯老师的话语中带着怒气。当时他讲的是,做人和写文章一样,要有大格局、大胸怀、大境界。他说自己的一个学生,大学时和女生谈恋爱,最后女生提出分手,那个男生把平时和女生在一起时产生的商场发票、餐厅票、电影票、车票,整整齐齐贴在一个笔记本上,让女生“报销”。我清楚地记得,他气愤地说,哪有人这么小家子气!这男生怎么这么个人!做人真不能这样!学生的做人与修为,同样是他古道热肠的关切。
“红柯”本为植物名,这种乔木材质甚坚重,耐水湿,耐腐,为水工、梁柱、车船、建筑的良材。良材负重,作家红柯的人生注定也是负重的,为文学负重,为责任负重,为良知负重,为社会负重,生命质感紧凑硬实,耐得住历史的冲刷。乔木红柯,站立是风景和标杆,倒下了仍是良材。作家红柯何尝又不是呢?骑手西去,红柯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