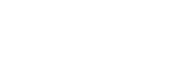农业大县的财政缺口:如何补偿粮食主产区利益?

5月中旬,河南滑县小铺乡的矮杆小麦田进入关键的灌浆期。(南方周末记者翟星理/图)
5月中旬,正是豫北平原的农忙时节,也是小麦灌浆期的关键时刻。
浇完最后一次水,种植户就做完了所有的农活。如果一切顺利,小麦将在20天后成熟、收割,售往全国各地。可眼前还有最后一个考验,这个时节易发高温、低湿的干热风,一旦出现会影响小麦籽粒灌浆乳熟。
在中国小麦产量第一大县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一喷三防”工作从2025年4月底持续到5月中旬。“一喷三防”是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混配喷洒,发挥防虫、防病、防干热风的作用。
滑县耕地面积约200万亩,其中高标准农田150万亩。“一喷三防”的中央专项资金有899万元,滑县农业农村局经过测算,这些资金只能喷洒99万亩耕地。
为保障夏粮生产,河南省要求“一喷三防”全覆盖,滑县完成这项工作的资金缺口尚有640余万元。
作为典型的粮食大县、财政穷县,滑县如何缓解这一财政压力?公众将目光投向一项尚未落地的国家政策——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即启动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加大对产粮大县支持,保护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积极性。
实际上,业界对此已经呼吁了很多年。2025年,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终于被首次写进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
资金缺口
滑县的耕地面积在河南省不是最多的,但这里土地平整度高,有最适合冬小麦生长的土壤,小麦产量多年来都是全国第一。
据安阳市政府网站数据,2024年滑县夏粮总产96.96万吨,平均单产535.5公斤。新华社曾在报道中描述,滑县一年的粮食产量够全国人民吃一个星期,够河南人民吃两个月。
滑县财政局农业股股长李丹说,就是这样一个产粮大县,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财政穷县。根据财政部刊载的一篇文章,滑县人均财政支出一度仅为河南全省平均水平的41.1%,全国平均水平的26.2%。
在粮食生产方面,中国小麦第一县每年可以获得多少中央财政补贴?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董相平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中央财政补贴分为项目型、政策型。项目型目前只有高标准农田建设,而且“金额变化很大,地方完全没有自主权。”
他解释说,中央对各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统一规划,每年确定各省的具体建设项目、面积和中央专项资金金额,“比如今年中央决定让你建多少,就给你多少钱,你根据拿到的钱去落实这个项目。”在滑县,这项专项资金2025年是一亿元左右。
政策型补贴历经多次变化,目前主要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农机具购置补贴。滑县财政局服务贸易股股长王喜兵介绍,前者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给农户,一亩地一年一百余元,后者由农户实报实销。也就是说,这两项财政资金,地方政府无权插手。
此外,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如果完成粮食生产任务,滑县还能获得一笔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但这个奖励是事后兑现,眼下没有。”董相平说。
正因为如此,在2025年4月底开始“一喷三防”工作时,滑县出现了640余万元的资金缺口。
“我们的裤腰带已经勒得很紧了。”董相平说。原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资金,按照中央的要求,必须优先“三保”,即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根据滑县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滑县财政民生支出52.9亿元,占比达77.2%,原因主要是滑县的户籍人口高达151万。澎湃新闻曾报道称,河南省内人口超过150万的县(含地级市)只有7个。百万人口以上可称人口大县,全国也只有186个。
滑县翻完账本,发现有一笔中央专项资金往年结余和一笔农业防灾救灾资金可以动用,但即便全部动用也还有215万元的窟窿。
为解决这215万元,“走投无路”的滑县动用了预备费。根据规定,预备费总额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明确规定用途为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为保障夏粮生产,滑县一次性投入了今年大约三分之一的预备费。
北粮南调
“如果这项政策落地,全国的高产穷县无论如何都能受益。”河南省粮储系统一位不便具名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只河南,高产穷县的问题在其他粮食主产区也普遍存在,“一个地方财政局的干部问我,‘为什么产粮越多,我们反而越穷?’”
他所说的政策,就是写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关于粮食产销区如何划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钰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改革开放后,东部省份在国家政策鼓励之下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加之在农业生产方面自然禀赋落后于东北、河南等粮食传统产区。在这一背景下,为适应新的粮食生产和流通格局变化,以粮食产量、人均占有量、商品粮库存等为指标,国家将31个省份划分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
目前,中国的粮食主产区有13个,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粮食主销区有7个,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产销平衡区有11个,为山西、宁夏、青海、甘肃、西藏、云南、贵州、重庆、广西、陕西和新疆。
随着2000年之后东部地区城镇化的迅速推进,主销区的粮食进一步减产,“新增的粮食产量绝大多数来自主产区,粮食增长向主产区的个别省份集中,趋势明显。”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蔡海龙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今,主产区承担粮食安全任务绝对大头的局面。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龙文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术界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粮食生产重心北移”。北粮南调的格局至此形成并持续至今。

滑县种粮大户王福强租赁了一千多亩耕地,他的小麦收获之后大部分将作为种子销售。(南方周末记者翟星理/图)
纵向补贴效应弱化
粮食生产重心向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集中,粮食主产区往往也是经济弱省和财政穷省,形成了独特的粮财倒挂现象。
蔡海龙用一组数据对此进行解释。从人均GDP看,2023年,主销区人均GDP为13.5万元,而主产区人均GDP为8.2万元,仅为主销区的60.7%,并且差距有拉大的趋势。
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看,2023年,主产区的人均预算收入为主销区的48%,两类地区人均预算收入的绝对差值由2003年的1241元/人扩大到2023年的7376元/人。
同时,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03年两类地区差值为1846元/人,而2023年差值为10348元/人,增加了4.6倍。
正是因为粮财倒挂现象愈发凸显,中央已经构建了纵向补贴的政策支持体系。
蔡海龙说,中央的纵向补贴以转移支付为主,主要包括价格支持、针对农民的各类补贴、对产粮大县的奖励补贴。
钟钰则表示,中央的纵向补贴具有明显的普惠制色彩。这些补贴不是专门针对主产区,大部分补贴项目是面向全国的,如农机具购置补贴、粮食保费补贴等。
一个例证是,滑县小麦产量冠绝全国,但其每年获得的中央专项资金,与邻近某县相当,而该县的小麦产量大约只有滑县的一半。
不过,钟钰认为,中央财政纵向补贴虽然有其功效,“但目前来看力度不够。”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主产区面临的“粮财倒挂”“高产穷县”等问题。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陈明星也研究发现,按粮食生产补贴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同期粮食总产量折算,2003年至2023年,平均每补贴1元所产生的粮食从34.2公斤下降到5.7公斤,每增产1公斤粮食需增加的投入从2004年的0.04元增长到2023年的0.11元。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央对粮食主产区单一纵向利益补偿的政策效应在弱化。
针对此种情况,200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提出,要建立健全粮食主销区对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2009年以来,关于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问题,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几乎均有论述。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十三个省(自治区)政协主席联名提交关于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提案。直到2025年的全国两会,这一机制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谁受益谁补偿”
在省级合作方面,地方政府已在数年前有一些探索。
2019年,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四省市签订共同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粮食产销合作战略框架协议。2020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签订储备粮调节市场、稳定粮价的协议。
主销区还尝试在遥远的主产区设置“粮食飞地”。
2022年,北京在河南、河北等粮食主产区建立市储备粮异地储备11.35万吨。浙江在东北三省一区建立粮源基地316万亩,省外储加销基地28个,加工线16条,在黑龙江、吉林、江苏、安徽等省委托代储粮食四十多万吨。天津、四川、福建等部分省份也出台了采购省外粮源运费补贴的政策。
这些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钟钰也发现,这些合作的模式是典型的互惠双向合作,“类似订单订购形式”。
龙文进补充说,省与省之间的产销合作更多地是一种相对市场化的运作,“侧重市场化的交易和项目的合作,基于市场价值和商业利益。”
而这与中央提倡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基本精神不同,“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更加注重财政资金的直接转移支付。它是建立在一个对粮食生产隐性成本,就是在市场价格中体现不出来的成本测算的一个基础上。”龙文进说。
2023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文件,2024年在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等5个粮食调出量大的主产省(区)开展试点,鼓励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多产多补的正向激励机制初步形成。其中“多产多补的正向激励机制”就包括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而目前参与试点的五个省份均未公开试点细则,因此无从知晓激励机制的具体内容。
不过,蔡海龙介绍,已经开展省内跨地市横向利益补偿的省份向外界提供了另一个观察样本。
2022年,江苏省南京市与淮安市签订60万亩优质粮食订单收购协议,每年安排400万元财政资金补贴淮安市。2023年,无锡市在连云港市建立优质稻谷、小麦保供基地60万亩,每年直接补贴连云港市财政资金480万元,在应急情况下保障无锡4万吨成品粮供应。
“谁受益谁补偿”的基本精神由此可见端倪,不过,如何准确统计调出粮食的流向和机会成本仍是实践中的一个难点。此外,在一些受访学者看来,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还面临着学理和现实的争议。
“这种利益补偿机制在理论自洽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龙文进说,学界也有观点认为不应该实施省级横向利益补偿,理由是粮食是全国性的公共产品,一般应该由中央财政直接负担。
龙文进解释,主产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复杂,从事粮食生产或许并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此外,主销区已经通过发展二、三产业向中央缴纳税收,中央通过各种转移支付至主产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一个责任。”
但南方周末记者在滑县采访期间,多位官员表达了不同看法。以滑县为例,土地已经开发殆尽,绝大部分拿去发展农业,二、三产业用地问题非常紧张,“不是我们不想,是不能。”
现实中的争议还有,2001年划分的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在最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各省的粮食生产能力已经出现动态变化。例如被划入主产区的某省,公开数据显示,近6年来该省粮食产量增幅不大,且其省内核心粮食产区还曾被权威媒体曝光其过去十年耕地面积锐减。
龙文进通过分析数据发现,部分主产区省份可能连粮食自给的任务都难以完成了。因此,学界也有呼声认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产区划分。
即便仍存在不少有待厘清的理论和政策障碍,但受访者都强调,这项制度的最终落脚点是“各地区都要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共同把饭碗端得更牢”。
种粮大户的期待
今年53岁的王富强是滑县有名的种粮大户,租了一千多亩地,还购置了大量农机农具,农忙时节能为一万多亩耕地提供有偿服务。卖粮收益和服务收益,是他盈利的主要项目。
但王富强坦承,最近几年,租地成本突破每亩千元大关,而粮食的市场价格常年稳定,卖粮的利润正在被逐渐压缩。
亩产的增长空间越来越小。近年来,滑县的小麦亩产增长至1100斤到1200斤之间。据央广网报道,2024年全国小麦平均亩产为396公斤。“滑县的亩产已经是历史极值了,除非农业科技大爆发,现在增长的潜力不大,增长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董相平说。
王富强的应对方法,是加大在农机农具上的投入。以他仓库里一台12万元的播种机为例,刚上市时他就和当地另一位种粮大户合计过,只要亩产增产100斤,以他们的种植规模,12万元的购置成本一年就能收回。果然,当年的增产就超过了100斤。
他解释,这台市面上最先进的机器配备了北斗导航系统,播种行间距、撒种粮一致,出苗率、成活率惊人。
“你问我挣着钱没,肯定挣了,但是都投到农机具上了。”王富强专门建了一个小仓库,放最值钱的农机具。现在,仓库里是两台大马力拖拉机和播种机,拖拉机每台也要二十多万元。按照农机具两三年出一次新产品的频率,下一次更新,他又要投入上百万元。
这个地道的滑县庄户,对种植户增收致富有着质朴的理解,“土地集中管理,控制地租,加大农机具补贴。”而这些方式,无疑都需要政策和财政的支持。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妍 杨昕 田忠鑫
责编 钱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