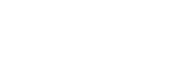全文!“两高”发布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
202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李剑、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副厅长刘太宗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发布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涉及实践中常见的法律适用争议问题,这些案件的办理体现了《解释》的精神,有助于对《解释》的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
案例一:上海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姚某假冒注册商标案
案例二:龙某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案例三:鲁某发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案例四:赵某年、张某燕假冒专利案
案例五:张某、孙某侵犯著作权案
案例六:刘某生、刘某侵犯著作权案
案例七:林某凤等侵犯著作权、刘某等销售侵权复制品案
案例八:汪某文侵犯商业秘密案
案例九:罗某、孙某东为境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案
案例一
上海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姚某
假冒注册商标案
【基本案情】
系乐高博士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为教育、培训、娱乐竞赛等。被告单位上海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店铺经营“LC乐高机器人中心”,被告人姚某系该公司实际经营者。2021年3月至6月,姚某将从他人处购得的假冒
注册商标的授权书、乐高教育教练资格证书等文件在店铺内展示,并将
等标识用于店铺招牌、装潢、海报宣传、员工服装、商场指示牌等处,提供教育培训服务。上海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收取培训课时费用51万余元,其中大部分收益由公司支配使用。
【裁判结果】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被告单位上海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姚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海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姚某系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遂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作出修改,将假冒服务注册商标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加大对注册商标刑事保护力度。本案认定被告单位提供的教育培训服务与权利人服务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属于同一种服务,以被告单位收取的培训费用作为入罪依据,符合刑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服务行业特征等实际情况,对“同一种服务”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规定违法所得数额为假冒服务注册商标犯罪的入罪标准,并进一步明确了行为人收取的服务费等属于违法所得。
案例二
龙某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基本案情】
荣某公司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医用隔离衣、手术衣”等。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间,被告人龙某、高某丰、陈某、袁某、曾某琴经预谋后,未经注册商标权利人荣某公司许可,购买防护服和包装材料后自行包装一次性医用防护服,贴附荣某公司的注册商标对外销售。其中,龙某负责联系购买包材,高某丰、陈某、袁某负责收购白板防护服,袁某还提供用于收取款项的账户,曾某琴联系用于贴牌生产假冒医用防护服的民房、聘请工人包装防护服等。龙某等人共销售一次性医用防护服4万余套,非法经营数额58万余元。
【裁判结果】
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龙某等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向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次性医用防护服”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医用隔离衣、手术衣”在商品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基本相同,相关公众认为是同种商品,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同一种商品”。龙某等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构成共同犯罪,非法经营数额58万余元,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遂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关于“同一种商品”的认定是假冒注册商标刑事案件办理的疑难问题。实践中,在行为人生产销售的商品名称与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名称不同的情形下,如果两者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种商品的,应当认定为“同一种商品”。本案依法认定侵权商品与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属于“同一种商品”,并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依法准确量刑,有效打击了制售假冒医用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同一种商品”的认定标准。此外,为依法精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解释明确了以共同犯罪论处的具体情形。
案例三
鲁某发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至2022年8月间,被告人鲁某发等人未经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委托他人制作“HARRY POTTER”“UNIVERSAL STUDIOS”等商标标识,并通过自行加工缝制、贴标的方式,生产制作魔法袍、围巾、领带等带有上述商标标识的环球影城哈利波特产品后予以销售,非法经营数额1125万余元。公安机关在鲁某发经营的场所内查扣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25730件,查扣吊牌、领标、水洗标等72550个。
【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鲁某发等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注册商标权利人注册了“HARRY POTTER”“UNIVERSAL STUDIOS”等商标,被诉侵权标识在“UNIVERSAL STUDIOS”后增加缺乏显著特征的要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属于“相同商标”。鲁某发等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遂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为进一步打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行为,统一和明确“相同商标”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相同商标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明确。本案中,被诉侵权标识增加缺乏显著特征的要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应当认定为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彰显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理念。
案例四
赵某年、张某燕假冒专利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某年、张某燕经营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起,二人在未经某中药研究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在其公司生产的化妆品包装上印制某中药研究公司“一种马齿苋提取液的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号,并销售假冒上述专利的化妆品。赵某年、张某燕销售假冒上述专利化妆品的金额为99万余元,查获尚未销售的假冒上述专利化妆品的价值为57万余元,非法经营数额共计156万余元。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赵某年、张某燕犯假冒专利罪,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年、张某燕开设化妆品生产企业多年,明知使用专利标记或专利号应经过专利权人许可,仍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产品包装上标注他人专利号,误导公众认为该化妆品是专利产品,属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情节严重,均构成假冒专利罪,遂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假冒专利罪规制的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虚假标记他人专利号使公众误以为其销售的产品系专利主体合法生产、制造的商品,损害专利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假冒他人专利的具体情形以及“情节严重”入罪标准,强化专利刑事保护。
案例五
张某、孙某侵犯著作权案
【基本案情】
2017年底至2023年1月间,被告人张某、孙某等以营利为目的,开发运营多款影视作品聚合APP。张某、孙某等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下载热门视听作品视频文件后上传至租用的云存储服务器,并购买他人的技术解析服务,通过其运营的多款APP向公众提供视听作品的播放和下载服务。通过技术解析服务,公众无需跳转至相关著作权人的网络平台,即可从上述涉案多款APP上获得该视听作品。张某、孙某等通过在涉案多款APP内以发布收费广告、收取广告推广费的方式营利。其中,张某、孙某等通过“盗链”方式传播视听作品7.2万余部。
【裁判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孙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向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孙某通过“盗链”的方式客观上使相关视听作品直接呈现在涉案多款APP上,属于作品“提供”行为,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从涉案多款APP获得上述视听作品并直接进行播放和下载,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行为。张某、孙某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视听作品,均构成侵犯著作权罪,遂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为实行行为,与“复制发行”并列区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侵害的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据此规定,行为人未经许可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录音录像制品、表演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随着信息传播领域的新型技术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类似“盗链”的技术可以避开作品上传环节,使用户获得相应作品,社会危害性大。本案基于“盗链”行为的具体方式及其社会危害性,认定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害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利于准确界定“盗链”等深度链接行为的性质。
案例六
刘某生、刘某侵犯著作权案
【基本案情】
2019年3月至2022年7月间,被告人刘某生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自行制作用于避开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的“加密狗”,擅自复制相关软件等,销售“加密狗”和盗版软件。刘某生又指使被告人刘某销售“加密狗”和盗版软件。期间,刘某生负责制作“加密狗”、复制盗版软件、上架商品、寄快递等,刘某负责账户客服、收款等。刘某生、刘某涉及非法经营数额分别为106万余元和14万余元。刘某生、刘某销售的“加密狗”可以避开著作权人为其软件著作权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
【裁判结果】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被告人刘某生、刘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生、刘某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故意避开著作权人为其作品采取的保护著作权的技术措施,特别是刘某生制作、销售“加密狗”及盗版软件等,在相关系列案件中处于产业链的源头,提供避开技术措施装置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刘某生情节特别严重,刘某情节严重,二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遂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纳入侵犯著作权罪的规制范畴,进一步加大对著作权的刑事保护力度。提供规避技术措施装置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属于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本案以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刘某生、刘某刑事责任,充分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彰显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服务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力度和决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故意提供规避技术措施装置、部件、技术服务的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案例七
林某凤等侵犯著作权、刘某等
销售侵权复制品案
【基本案情】
2019年至2023年2月间,被告人林某凤等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采用扫描、排版、印刷等手段,复制发行“剧本杀”作品,非法经营数额540万余元。被告人刘某、杨某、杨某主明知林某凤等人出售的“剧本杀”系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侵权复制品,仍采购后对外销售。其中,刘某销售金额738万余元,杨某、杨某主销售金额312万余元。
【裁判结果】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林某凤等犯侵犯著作权罪,被告人刘某、杨某、杨某主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分别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某凤等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文字作品及美术作品,均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刘某、杨某、杨某主销售侵权复制品,均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遂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入罪规定,将“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修改为“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扩大了入罪情形。为进一步打击侵犯著作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入罪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销售金额”“货值金额”“复制件数量”为“其他严重情节”。为进一步区分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司法解释明确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不包括单纯“发行”行为。以出售方式发行他人制作的侵权复制品的,应当认定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本系列案根据各被告人实施的具体行为,分别以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定罪量刑,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
案例八
汪某文侵犯商业秘密案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间,被告人汪某文在芜湖某汽车公司任职。2021年3月23日,汪某文准备跳槽至浙江某新能源汽车公司,从事电器研发工作。为了将芜湖某汽车公司的开关控制技术带至浙江某新能源汽车公司,2021年4月4日晚,汪某文将其无权限查看的芜湖某汽车公司智能车技术中心一组、二组组长的电脑硬盘拆卸后带离,将电脑硬盘中某型号汽车开关系统的“中控台开关总成”“一键启动按钮”技术资料上传至自己的百度网盘。经评估,上述两份技术信息的合理许可使用费为114万元。
【裁判结果】
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汪某文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向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芜湖某汽车公司某型号汽车开关系统中的“中控台开关总成”“一键启动按钮”技术图纸所载技术信息,属于商业秘密。汪某文以拆卸带走电脑硬盘的方式获取商业秘密,属于以盗窃的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可以按照该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认定损失数额,情节严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遂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入罪标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修改为“情节严重”,加大对商业秘密刑事保护力度。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人因此前并不合法知悉或者持有商业秘密,其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行为本身就具有不法性,应当予以严厉打击。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可以按照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数额,不要求将商业秘密用于生产经营造成利润损失。本案根据刑法规定,认定汪某文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并依法判处刑罚,彰显对创新成果的严格保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
案例九
罗某、孙某东为境外
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案
【基本案情】
2022年8月,被告人孙某东接受境外人员委托,为其有偿提供某科技公司新能源电池的商业信息。孙某东经与被告人罗某商议,罗某以刺探、收买等非法方式从某科技公司相关人员处获取该公司关于新能源电池研发数据、未来产业布局等商业信息,孙某东提供给境外人员。孙某东收取报酬11万余元,将其中7万元支付给罗某。2023年4月,罗某直接接受该境外人员的委托,再次提供某科技公司商业信息并收取报酬10万元。
【裁判结果】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罗某、孙某东犯为境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东、罗某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的新能源电池研发数据、未来产业布局等信息属于商业秘密,罗某、孙某东构成为境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遂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完善刑事法网,加强对商业秘密刑事保护。本罪系行为犯,不要求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即可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该罪升档量刑标准“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入罪情形等保持一致,确保两罪定罪量刑的有效衔接。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